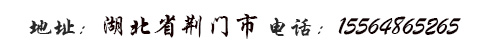物志芙蓉诗与芙蓉画
| 霜降后,又到了成都芙蓉满城绽放的时节。正值第四届天府芙蓉花节,成都植物园如约举办一系列与芙蓉相关的活动,其中便有“芙蓉·名人堂”系列讲座,而前来听讲的喜欢芙蓉的市民,提得最多的问题,便是关于中国人的芙蓉接受史。明,沈周,《卧游图册》之芙蓉花一要谈到中国人的芙蓉接受史,或许应该以唐以后的木芙蓉意象的出现为分界线。在此之前,广泛存在的是莲的水芙蓉意象。但这并不是水芙蓉与木芙蓉栽植的分界线,唐以前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水芙蓉与木芙蓉并存的周期,所以诗文中的芙蓉意象究竟是木芙蓉还是水芙蓉,的确需要我们细细鉴别。这是芙蓉留给我们当代人的一个难题,但也无妨看成是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事实上,像这样“一花两意”的现象,在中国的花卉图谱中并不多见。仅就楚辞中出现的芙蓉来考察,芙蓉最早在诗文中的出现,不脱“香草美人”的审美意象。“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楚辞·离骚》)”中的芙蓉是香草美人的象征,“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楚辞·九歌·湘君》”中的芙蓉也是,“美人”在这里的指代,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女性角色,而隐隐有君子的象征意义。穿上芙蓉做的衣裳,屈原大胆而瑰丽的想象,为芙蓉在民间的意象接受提供了最初的标准。沿着“香草美人”的意象发展,建安文人的诗文中出现的芙蓉开始有了相思的意味。曹植《涉江采芙蓉》首句“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是一种“上承”屈原的意象,但到了下一句“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就有了新的意象生发,是一种“启下”的意象。芙蓉作为爱情之花大约是从这里开始的,相思大约是爱情中最初始也是最美好的阶段,到了后蜀主孟昶跟花蕊夫人色芙蓉情缘,其朦胧的相思意象已经升华成浓烈的爱情意象,至于曹植相思的是否是甄夫人这个公案,早已经不重要了。再往后,王粲在《清河作》里,写“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便以强烈的明艳色彩对比,写出了芙蓉明艳的特别之美,写入芙蓉审美接受史,对芙蓉的后世审美影响深远。唐朝尚丰肥浓丽,重瓣芙蓉与牡丹的花姿相近,使芙蓉的审美接受多少受到了牡丹的影响。这样一种提携的关系,大体注定了芙蓉在中国花卉史上的品阶地位,使她既不在四君子主导的前十之列,也不至被甩在少人问津的末序。这样的地位,当然不至为她招来嫉恨,自然也不会让人彻底遗忘。如果说“中庸”是中国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那么,芙蓉的天赋禀性使她天然地在百花园中占据了“中庸”的有利地形,这与庄子所谓山中大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是一脉相承的生存逻辑。这样的生存逻辑,在钱锺书先生看来,不啻一种天赐的“保护色”。《管锥编》册二《太平广记》第一百一十四之“诗咏保护色”:王昌龄《采莲词》云: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花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又,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一二《四望亭观荷花》:面面湖光面面风,可人最是白芙蓉。分明飞下双双鹭,才到花边不见踪。都是保护色的意境。芙蓉保护了像芙蓉花脸一样的美人不被围观,或者像芙蓉花脸一样的美人保护了芙蓉不被采摘,这种相互保护的关系,正是芙蓉“中庸”生存逻辑的另一面,钱锺书先生溯源明流,阐释古典诗词创作中的写景状物技巧及其所具有的文学意蕴和情感内涵,一开新见,是真懂芙蓉花者。元,陈琳《凫溪图》二从数字上看,芙蓉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中的出现频率并不是最高的。潘富俊《草木情缘》中所罗列的数据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不妨拿来作为参考:芙蓉在先秦文学中出现,大约不超过3次。魏晋南北朝为2次。全唐诗为16次。宋诗钞和全宋词加起来一共57次。元词及散曲加起来18次。明朝是一个高峰,全明词及散曲加起来次。清代小说及诗词散曲为19次,呈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这当然因应了诗词散曲这一类古典文体的逐渐退出、白话文逐渐普及的规律。总体来看,古典文学中的芙蓉,总共出现次,这个数据和动辄数千上万的梅兰竹菊桃李芳菲相比,确实少了很多。以明代最多次作为观察入口,我们大体可以看出芙蓉在明代接受观念的演变:明人张谦德《瓶花谱》“品花”条,将芙蓉列为六品四命。按其“九品九命”的升降法,一品九命的兰、牡丹、梅、腊梅,各色细叶菊、水仙、滇茶、瑞香、菖阳为最高,是一品九命。芙蓉之六品四命,中偏后。而在明人袁宏道的《瓶史》中,芙蓉则作了木樨的婢,这又比张谦德对花的品阶定位更具有文人的个体审美趣味,其主仆之分当然是立足于插花艺术的,并不能作为那个时代的主流审美标准。但芙蓉由于花朵繁大而且厚重,很难插瓶则是插花人的共识。对照五代张翊《花经》对芙蓉“九品一命”的品阶,张谦德对芙蓉品阶认定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跃升。在这个序列里,芙蓉沦落到和牵牛花一样的地位,不能不为之一叹。考虑到明朝是文人审美的高峰时期,张谦德对芙蓉“九品一命”到“六品四命”的捞取,代表着一种主流审美的回归,似乎也在呼应着屈原开启的“香草美人”意象。要注意小说这个文体对花卉叙事的影响。由于叙事局限的突破和文字的放开,文人在大容量的小说文字空间里有更大的社会生活表达自由,《金瓶梅》和《红楼梦》中,大量出现插花、赏花的场景,而曹雪芹则干脆在小说中以花喻人,《芙蓉女儿诔》可能是芙蓉唯一一次进入到祭文这个文体。但读这篇饱含深情的祭文,我们丝毫感受不到作为本体的芙蓉的尴尬,反因为她得以进入神仙谱系而倍感荣耀。“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这篇祭文的核心便在这里,这是曹雪芹对晴雯对黛玉的最高礼赞,也当然是对芙蓉的最高礼赞。有了这一片祭文,历代文学中的出现频率,明代文人的品阶认定,已经不重要了。陈子庄《芙蓉》三历史上的文人,只要进入写物的大环境,总免不了“文以载道”或者“诗以言志”,这背后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古典传统。写芙蓉,大约也离不开这个传统。范成大写《窗前木芙蓉》,说她:“辛苦孤花破小寒,花心应似客心酸。更凭青女留连得,未作愁红怨绿看。”任凭青女逗留多久,木芙蓉绝不会畏缩屈服。这是一种典型的借花抒怀,表达自己虽然漂泊而未逢时,但决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意志。写这首诗的时候,范成大应该正是意气风发、昂扬不凡的年纪,诗人巧妙地融物以情,喻己以物。芙蓉的君子意象在这里流露无遗。东坡写《芙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yea.com/mfrypzff/11283.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天学习一味中药冬瓜皮第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