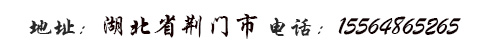我的知青生活二
|
作者简介: 易晓虎:男、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68届知青。修过铁路、下过煤矿、干过工会、当过车间主任。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五十年岁月早己淡化了当年,不知不觉间,老了我意气风发的年华。过往都相继褪色,能够触摸并感受到的,也仅剩下记忆的余温。 二、农活——苦力活 次日早天刚放亮,当我们还在蒙头大睡中,队长已将那两扇低矮的破门拍的震山响了。在一阵阵的哈欠声中,我们极不情愿的爬起来。“城市的娃们事就是多,起来了还要洗脸呀、刷牙掐,还要烧热水哩……”在队长的声声抱怨之中,我们跟着一众村民来到了田间地头。说起我们这位队长实在不敢恭维。印象中的队长应该是电影“青松岭”李仁堂形象,威武、豪迈、高大、伟岸,嗓音宏亮,掷地有声。现实中我们这位队长,小个子、斑秃头,长相丑陋,一双小眯眯眼迟早看眼角都堆着一滩眼屎,穿着一条能将他整个人套进去的大裆裤,外罩一补丁累累对襟短袄。且不分田间地头,不管任何场合随处便溺,在将大裆裤提至短脖下时,左右对折后,再次将外罩短袄左右叠压,左手压着衣边,右手用一条黑不溜秋的长布带子围腰间缠绕两圈,再一个吸气收腹绑扎,便完成看似复杂却被他一气呵成的轻松搞定。 其实,陕西农村男人基本都这打扮,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我们队长却是男人中的另类,个头小、斑秃头、眯眯眼也到便罢,他还走的是八字步,老远便能听得到他“踢沓、踢沓”的脚步声,双脚永远在村道各处画八字,鞋内“娃他舅”(既脚大拇指)尚未露面,他“舅爷”脚后跟却早已是灰头土脸了。时值严冬,每逢出工下地他不像别人将铁锹扛在肩膀。而是将双手筒在袖子中铁锹夹在腋窝,且锹头向后冲上、锹把向前冲下。配上污浊不堪的棉袄、破烂不堪的吊裆棉裤颇显衣衫褴褛。我当时常常暗自琢磨皱眉,怎么选这么个人当队长,村里那么多比他强百倍千倍的人有的是,难道就因为他是三代贫农……。然,随着接触的日益增多,了解的逐渐加深我不但舒展了眉头,更心生佩服与感激了。 在农村每天出工参加劳动得到的不是钱,而是工分。更不是现代人概念中的月底某日发工资,领到手的是现钱。而是年终按当年收成好坏评定每分所值。收成好每分所值就高,不好每分所值就低。生产队按壮劳力、青少年、妇女划分三个评分标准,既:壮劳力每出一天工记10分、青少年每出一天工记8分、妇女则记6分。而我们初来乍到的城里娃,一个个细皮嫩肉,韭菜麦苗不分、五谷杂粮不辨,自然评8分了。因为所在地处平原,盛产粮棉属较富裕地区,当年每个工分合0.12元、若按我们每天8分记,全年天都在出工,年终既可分得.4元。这在当下人可能不屑一顾,可对于当年的我们那是一笔可望不可及的巨款。即便如此我们往往还拿不到五分之一,因为年终队上要扣除每月领到的口粮、蔬菜、棉花款。更何况我们还缺勤呢。这已经算很好的啦,和有的山区贫困队比,我们很知足了,起码干一年多少尚能给家里拿点,我们的师同学还买了一辆自行车,令我等好生羡慕。而绝大多数知青却没有那么幸运,往往在田间地头辛劳一年,盼到年终非旦分文不取,反倒欠生产队一笔钱也不足为奇。 六十年代农村劳动工具非常落后,没有机械,一切农活全靠人力。队上唯一的一辆大木轮牛车(用木头做的轮子外面套上铁箍)虽说也能载个千而八百斤的,但队长不到紧要时刻是绝对禁用的,牛是专业饲养员喂,车由专业车把手驾驭。两年多,我们只有起圈拉牛粪的份。 刚开始我们也只是跟着象征性的平整下土地、铲草、锄地、推车等,干一会就找个背风朝阳的地方,与村民围坐在一起听故事,讲笑话。感觉还真如个别村民所说“农家活、慢慢磨”。 每日收工后或下雨天,我们的房间便会聚集三五村民。随着交往的增多大家在一起便显得轻松了许多,没有了之前的生疏与拘谨,气氛显得融洽又快活。大家相互介绍并戏谑取笑着对方,且不时夹杂一些脏话调侃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往往召来一些村中游民围在门外,个个双手插在袖筒站在门外不时伸头,想要知道里边阵阵传出的笑声。还有人踌躇着要抬起手搔头,不觉将双臂举了起来,突感觉不对,立刻又放了下来,人不由得往后退了两步,露出一脸的尴尬。 村民们还有一项农闲时的娱乐活动叫“丢方”(也称土围棋,在中国流传至少有几百年,几乎遍布西部各省,仅次于象棋。虽规则简单易学,内里却变化多端、博大精深,属易学难精之优秀棋种)。既随地划一大方块,再分成若干个小方格,构成一幅方格棋盘。就近折个树枝,对方也就地捡些土坷垃。选一背风朝阳地,双方对面而蹲既开始博弈。既a方有四子在同一条线时(横、竖、斜即可)就可在对方棋盘中随意拿掉b方俩棋子,称四线。如果两头是a方棋子,而中间是b方棋子,a方就可以拿掉b方中间的两子,称夹。最后以多子者为胜。每逢此便引来无数旁观者围拢观战,有时还能引发打架。且说那日又有几位村民在我们后院展开丢方,同样有几位村民围拢左右,此时一方可能连续输了几盘,便对背后弯腰神态专注观战的人说,“你知道咱老陕把太阳叫啥不?叫爷!你把爷档住了”。观者岂肯吃亏,一来二去便打了起来。但只消稍加劝解立马就没事了。毕竟是一个祖先,看着年龄相当却可能是爷与孙子或外甥与舅。 固然,我们也有发生矛盾时,也弄过许多笑话。冬天外面冷风嗖嗖,为解决起夜问题,买了个瓦盆。大家按次序排,每人次日早晨将一瓦盆尿端至后院数十米处的茅房(厕所)倒掉,月余一人一天、一天一倒相安无事。岂料一人回家半月,回来时却怎么也掰扯不清该如何轮到他了,无奈便让其从某天晚上撒尿起算。其得了这句话便每日下午起便停止喝水,临上床前一小时频频去茅房,站着尿完还要再蹲着尿,恨不得将尿泡用双手拧上几圈。到晚上就控干净,一滴都不尿。然毕竟尿泡不是长在别人身上的,一日终将憋不住的他,半夜起床,但却奔了后院的茅房。次日晨谁都不肯倒了,放至晚上临睡觉前拖不过,其竟然将倒了一半还余半盆尿又端了回来……。为此,我们大家便寻思着整治他一下。是日,见其拿本书去位于后院的茅房。农村的茅房都是依墙角落挖一土坑,两面用土坯垒成约1,5米高﹂形土墙,留一进出口,在出口处放一破铁锨,有人进去便会将铁锨斜靠在入口,出来会扶正靠墙放。大家约定俗成只要看到有铁锨斜靠着,就不进去。后院有一棵核桃树,枝叶茂盛,将茅房几乎覆盖,使原本露天的旱厕增加一片绿荫。但从未结过果,却结了好大一个马蜂窝。平时我们唯恐避之不及、轻易不敢招惹。次日见其入内,并将铁锨斜靠在门口,便从口袋掏出弹弓,照准那硕大的马蜂窝连发两弹,发发命中。我们立即窜回房内,并将门插上。片刻,就听外面大呼小叫,先是人与铁锨同时倒地声,接着一阵急促的奔跑到了门前,推不开门,又嚎啕大哭着与盘旋在头顶的群蜂飞奔向前院……。后在房东大爷也身中数彩的奋力驱赶之下,群蜂方高奏凯歌返回巢穴。 此事不但惊动了全村,更招惹来其父母亲。当看到儿子鼻青脸肿翻翻嘴时,气愤的对我们大加斥责。此时,我们方意识到这场恶作剧的确玩过头了!虽然后期仍有发生摩擦,但我们都很注意分寸了。 往事并不如烟,若干年后我们见面笑谈此事,这位校友依然狠狠地说,你们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了,知道吗我至今还怕到连蜂蜜都不敢吃呢! 当地村民民风淳朴,即便生活单调日子艰苦,人们还是那么的勤劳、善良、肯干。他们每日辛辛苦苦、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在田间地头干农活,每个人有多少力气就出多大力,不偷懒、不偷奸耍滑。农忙时就围坐在地头田间吃饭,无论饭菜好坏也从不挑剔,依然吃的很香。其实,当年在农村的孩子更辛苦,他们的童年是在土炕或土地里滚大的,稍微大点便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挣每日的6分工(合0.70元)。如若没有个人后期的奋斗或家里在外面有一定社会关系,他们则是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头直到干不动终老为止。一生无节假日、无劳动保护、冬无取暖费,暑无降温费、无年假、无八小时工作制、更无加班费。他们的假日要老天爷说了算的。所有这些个无,不知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情何以堪做何感想。 农活没有轻松的,劳动的项目也层出不穷,总之一切围着土地转。例如看水,既冬灌。听似轻松,白天不用出工,夜晚夹一铁锹巡查在田间地头。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恨不得将自己裹成粽子。那几年雪下的有一尺厚,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一片白茫茫的,树上也挂满了雪。哈气成霜,冷风呼啸着,万籁俱寂。一望无际的看不到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的沿着地畔一路走,一路看,生怕宝贵的冬灌浇地水出现渗漏跑掉。有时稍不留意,看似平平的土地实则表面结着一层薄薄的冰,下面却是被水浸透的稀泥,一脚下去鞋子湿透,刺骨的寒气立马从脚心冰至头顶。想休息一下只能蹲在地头,但不消两分钟便自己跑起来,否则会冻僵了。 所有这些表象尚可忍受,唯心中某种恐惧在如影相随。村民说在附近有狼出没。据说有一种禁忌,不得悄悄地从后边拍别人肩膀,说狼会从后面悄悄地跟踪人,靠近后会立起前爪搭在人肩膀上,人若一回头,狼就会咬住人的咽喉要害,人便立马毙命。虽说不辩真假,总感觉挺害怕的。且村中早年的确有人是被狼咬伤,并留下极其惨不忍睹之面孔。 黢黑的夜晚,四下里荒草丛生、黑影朦胧,哪怕是踩断一根枯树枝,也能把人吓到毛发耸立、后背发麻。心里老想着草丛、树影后会突然跳出来一只狼。一晚上心都是紧绷着,直到天亮了才将那颗扑通扑通乱蹦的心放下来,人方才平静了许多。 艰苦的冬天总算熬过去了,转眼时光进入六月份,我才真正领会了什么叫农家活,什么叫龙口夺食、什么叫大战三夏,什么叫战天斗地。 农村的盛夏,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太阳拼命的向地面挥洒着它的酷热,地里的人们被蒸腾在热浪中,心如火烧、汗如雨下,个个埋头挥舞着镰刀。随着一捆捆金黄麦穗被挑上车,我的汗水也如注般的流了下来。艰辛漫长的夏天再也不是我儿时嬉戏的乐园,毒辣的太阳将我晒得面部黢黑,强烈的紫外线将我灼的肩背爆皮,在汗水不断的冲刷下,钻心般的痛。晚上在忍受酷热的同时,还得喂养一批蚊虫跳蚤。感觉收麦子应该是天下最劳、最累、最扎、最难受的一件事,一天下来人困马乏,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无力至极、酸痛直至。 随着日渐对农活的熟悉,队上将我们工分升至为10分,既当做壮劳力来使用。每日在黄土地劳作的重负压在我18岁稚嫩的肩膀钻心的疼,每晚收工,当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房子时,仍无法休息,还得生火做饭。得挑起水桶去村西头的水井房,从十几丈深的井里绞水。从井口往下看,里面是黑沉沉的深不可测、望不到底。上盖一简易草棚遮风挡雨算作井房,井口上方搭一木架子,架一辘轳,卷起一大卷大拇指般粗细的绳,绳的两端系用牛皮拧成,均拴一铁勾,各挂一水桶。辘轳放下时,随着“咕噜、咕噜”声响上一阵,直到把大卷的绳放完,听到“咚”的一声、再稍候片刻,始采用弓步使劲转动辘轳把手,一下一下的慢慢绞起,绞动辘轳时一只桶上一只桶下,两小桶倒一大桶。每次得约5分钟方能打满。遇晴天还好,若雨天再看那打上来的水是昏黄的,甚至于还有些细小微生物漂浮在水里。绞水的辘轳把是按照绝大多数右手人设计使用的,只是苦了我这个左撇子了……。 好在我打小担过水,自认为肩膀还算硬朗尚可承受。但没料到走在凹凸不平,蜿蜒崎岖,晴天硬如刚、雨天赛泥浆的村道竟然东倒西歪,一会便将人弯成了大虾。不足米距离就歇了n次,而且是边走边洒,到住处只剩下两个半桶了。这一切自然会引的个别村民嘲笑。此时,队长必然首先站出来,在斥责个别村民的同时,会抢过扁担一口气给我们担回去。然后会两眼眯缝着,把手背到背后说,“你们才多大的娃呀,你爸妈咋放心把你们撇到咱这农村,连水都担不动,还咋做吃的呀”。 俺爹俺娘俺家乡由央视纪录片导演郭西昌(子星)创办 独一无二的家乡,独一无二的爹娘,把你们的思念告诉我,把我们的情感献故乡。 欢迎各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yea.com/mfrysltx/8827.html
- 上一篇文章: 神奇的中草药夏枯草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