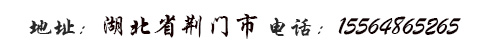旧时光阴里的古法榨油
|
哪家白癜风医院权威 htt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旧时的榨坊一直到榨油机的出现,几年功夫就退出了农副产品加工的舞台。 我直到读完高中,回乡参加集体劳动,才有了对古法榨油的体验,有了对榨具名称及操作术语的了解。 本文仅以榨茶油为例。榨桐油、核桃油大致相同。 上焙 每年大约农历十月,油茶林里的茶籽收捡得基本干净了,油榨就开榨。农户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油茶籽搬到油榨里焙灶上焙燥。焙灶通常有两眼,都是用泥坯砖筑成的,齐胸高,约八尺见方,上面用木框镇着一方以均匀间隔的四根木杠托着的篾笪。木框深约八寸,可以摊放八箩茶籽。如果不够八箩,木框中间可以插入间板分隔,和别户人家合伙同焙。两眼焙灶焙燥的茶籽刚好一日可以榨完。焙灶对着碾盘的一面留开灶膛,一是方便碾场里的人边推碾子边看火,二是方便把焙燥的茶籽搬到碾盘里碾压。 茶籽在焙笪上填够了,摊平了,就可以用硬木柴在灶膛里烧火开焙了。俗话讲,独木冇燃火,灶膛里至少要两根硬木柴相伴着烧。只要看见火舌朝着焙笪下面的空间钻,焙笪上面腾起雾气而不是冒青烟就恰到好处。这时候千万不要把干草、干叶等易燃物投入灶膛,以免火力过猛,引燃焙笪漏落的粉尘,延及焙笪和受热的茶籽。况且,火力过猛,会把茶籽里的油脂焙融,反而包住水分不能蒸发,到后面经不起压榨,俗语讲容易“拉屎”,降低了出油率。摘果的茶籽出油率通常在28%左右,捡拾自然迸落的茶籽出油率可达30%以上。 从清早焙到黄昏时分,看到焙笪上表面的茶籽都没有水迹了,趁着天还没有黑,就赶快翻焙。就是把灶膛的柴火移开,把上层刚受热的茶籽装入几个箩筐,把下层受热已久的茶籽装入另几个箩筐。然后把上层茶籽倒入焙笪摊平,再把下层茶籽铺在上面,继续烧火接着烘焙。这样就把燥与湿互换了位置。不然,燥的燥过了度,湿的终究是湿的,不能达到平衡统一。后面就要均匀地续火,一直焙到黎明时分,就要“抽样检验”,即是随手在各处拈出几颗茶籽,放在木框上一拍,若一巴掌拍碎,茶籽肉碎裂成粉末,表明恰到火候;若拍得扁而不碎,茶籽仁还稍显淡绿色,表明还没有充分焙燥;若拍得木框上粘了油迹,表明“焙老了”,会影响出油率。 这些上焙——看火——翻焙——守焙——下焙的顺序和程度都是聪明的古代劳动人民总结预算好了的。 “守焙火”是一项夜以继日的艰苦劳动。在集体时,每夜安排两个人守焙火,以便轮流睡个囫囵觉。油茶山承包到户后,我家责任山连年丰收,每年都由我一个人连续几夜守焙火。好在那时年轻,能吃苦耐劳,挺过来了。现在老来好睡,也许是要把那时因各种原因耽误的睡眠补回来吧。 闲散人员是不许来焙火边向火的,或因慌张踏入火塘,或因安闲自在打起瞌睡而栽入火塘,或因不明事理丢杂物入火塘,都后果严重。再则,闲散人员势必给专事守焙火的人造成障碍。 碾粉 在焙灶与榨场中间设置一个碾盘。碾盘是一个约八尺半径极规则的圆。沿着圆周敷设一圈石头打制的碾槽,俗称“槽岩”,以黄泥掺石灰筑牢。在圆心上竖立一柱木桩,俗名“将军氶”(这个“氶”字只代表方言语音,准确的字形是“木”字无头,唯《康熙字典》“木部”收载,其意是被打翻了头的木桩)。在木桩约三尺高处箍定一根檩子粗略长于碾盘直径的可以绕着木桩旋转的横木,俗名“排杆木”。排杆木尖梢的一端用一块内圆外方的木头,俗称“升子木”,把约三尺半径的俗称“子岩”的石碾穿接起来。 焙好的茶籽分四次撮在碾槽里,用像小船的桨一样的长木块,俗称“木油匙”,把茶籽扒拨均匀。除掌榨的油匠师傅要捆扎包草、清理尖码和油圈、烧火滚甑脚水以外,打油的人就以轴对称的方式排开,推着排杆木,驱使石碾以逆时针方向在碾槽里滚进。刚被碾压的茶籽发出“喳啦喳啦”的轻微响声。被碾碎的粉末被挤压而沿着碾槽壁向上冒,还未被碾压的茶籽則纷纷滚落碾槽底部,接受碾压。听不到“喳啦”声响了,就由一人用木油匙翻动粗油粉,用竹扫把将包藏在油粉里的茶籽和较粗的颗粒轻轻扫入碾槽。如此多次,直到全部被碾成“鹅毛粉”。 民间把推碾子的劳动编出一则谜语:“一根棍子拍(挑)簸箕,大路冇行行圳基。清早起来行到黑,还在这个圆圈内。”棍子就是排杆木,簸箕就是碾子,圳基就是碾槽两边黄泥拌石灰所筑的挡墙。这种运动,像行星运行,周而复始,长在路上,须臾不歇,无所谓起点,无所谓终点,分不清谁在前头,谁在后头,面前始终挡着一根横木,既不可超越,也不能离弃。 据说有的地方用牛套上牛丫缆绳来拉碾子。但是,每当发现牛竖起尾巴,张开后腿,即将拉屎拉尿的时候,赶牛人往往用某种器皿去承接,却或是来不及,或是只接着一部分,难免把污秽溅入碾槽。还据说,拉过碾子的牛,机械地绕圈行进,以后下田耕作竟然不听使唤了。 碾盘是圆形的,却设置在正方形的屋子里。所以圆与外接正方形的接点处是最逼窄的地方,不是推碾子的人不可随意经过这些接点。明事理的人要经过这些接点,会依着逆时针方向,趁排杆木越过逼窄点的瞬间,随后经过。这和车辆行人靠右走一样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还在集体的时候,我们寨子新建一座榨坊。本地木匠都没有经验过这种工夫,只好从外乡请来一个哑巴木匠。就在竖立碾场中间这一扇屋架的时候,“卉”字形的构造,中间没有柱子落脚,我们人多,却不知在何处用力,大家都干着急。哑巴师傅脚踢一堆木杠,手拉一根篾条做缠绕之势,口里呜哩哇啦地“解说”。经过哑巴师傅的“指手划脚”,我们茅塞顿开,用篾条捆扎几根木杠在屋架上做“假柱子”,大家才找到了着力点,很快就屋架竖立起来,扎好支撑,然后解下木杠。所以俗语讲“胍有胍的巧,瞎有瞎的乖。” 当茶籽被碾成“鹅毛粉”的时候,基本与地面持平的蒸锅里的水也开了,木甑内热气腾腾,油匠师傅发出“上粉”的指令。人们就七手八脚把碾槽里的油粉撮、扫、装进箩筐。先向油匠师傅弄好的蒸甑里倒进一箩油粉摊平,并使周围高,中心低。因为蒸汽沿着甑壁上升得快些。原来甑底的十字架上垫了一个篾笪,再摊开两捆包草,又覆上一个篾笪。一是不让油粉漏下蒸锅里去;二是使包草由燥变湿,增加韧性,且少吸油。看到第一箩油粉表面由黄褐色变为红褐色,甑内到处冒着热汽,村寨中到处都能闻到茶油的幽香,这表明第一箩油粉已经蒸“熟”了,接着又向甑内加进一箩,依次上完四箩,就有满满一甑。蒸的过程只是把油粉加热,油粉并不吸收水汽。 油榨里的工夫安排得紧张有序,环环相扣,瞬息不误,与现代的流水作业相差无几。第一轮油粉全部撮起,紧接着又把第二轮茶籽摊在碾槽,又推动碾子碾压,直到油匠师傅把头一甑油粉全部包成油饼,装进榨梁木的榨膛内,发出“打油”的指令。所以,一进入榨坊,就人人有事做,时时不空闲。 打油 头一甑油粉全部蒸熟,上面覆盖的两捆包草也湿润发软,油匠师傅就喊“装粉啦”。立即就由一个人手执小型撮箕,另一个人挥动铁铲凭手感把油粉撮满撮箕,因为要使油粉保持高温,蒸锅下面仍然火力不减,甑内热汽腾腾,是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执撮箕的人两手提着撮箕的系绳走到油匠师傅面前,立即灵巧地一簸,变换成双手捧着撮箕边的状态,把油粉倒在用篾扎的油圈和糯稻草“砌”成的“窝”(像个大鸟窝)里。油匠师傅立即用双脚把油粉踩紧。他三脚四脚就踩好,装粉的必须赶快送来第二撮箕。不然,他会大声呵斥:“唉,你两个比老娘子生崽还难哪!”如果装少了,他会问你:“怕是跟你借盐不是?”如果装多了,他又训你一句:“要么就饿死了,要么就胀死了!”所以初次装粉,一时还把握不准这个度。第二撮箕油粉送到,他两脚踩紧,并把包草从外往里踩熨帖,取下底圈和顶圈,就成一个饼,搁在另一边的码子上。包完一甑油粉,大约有十一或十二个饼。随后,他把油饼一个一个端进榨膛,侧立,整齐均匀,推紧,加上一个厚厚的木饼,再加一个四四方方的“大码子”,大码子旁边预放一个前小后大的“倒贯”。接着把两个长尖码分上下两层异位插入木饼与倒贯之间,就喊“打油啰!”。蒸甑里的油粉撮空,打扫干净,撮油粉的一人学着油匠的方法“砌甑”,一人往蒸锅加进一桶冷水,两人再把木甑抬在蒸锅上,一是防止有人慌张踏入蒸锅,二是罩着蒸锅不易散热,以利赶上蒸第二盘油粉。 大约一丈有余柱子一样粗的椆木做成的油柱,中间凿一个“”形相对的孔,装上活动栓销与摇把连接。摇把上端挂在粗藤卷成的“O”形环上,吊在两把木“╳”架起的横木上,和物理学所讲的“摆”是一个原理。油柱上绑着四根缆绳(棕缆,麻缆,草缆均可)。八人或六人每两人一对,齐心协力拉动油柱向后上方荡扬。反作用力使油柱向前下方回落,前三对人同时向前方牵拉缆绳助力。油匠师傅則双手抱着油柱准确地向尖码冲撞。这时如果扯尾缆的人用错了力,油柱头会向上扬,熟练的油匠会踮起脚尖或干脆耸身一跳抱着油柱,决不失手。但他会责问:“扯尾缆的吃饭多嘎,冇得气力消是吗?”尖码被步步楔进,油饼被渐渐挤压,在高温高压下,油液透过包草的缝隙,沿着油圈沥沥淌下,如檐注一样纷纷滴下油槽,以“滴水成河”的态势流过油舌,注入油桶。 榨出一部分油来,油饼内区域松弛,压力减轻。油匠师傅继续指挥打紧上层,松开下层,加进码子;打紧下层,松开上层,加进码子。如此反复递增,交替轮换,循序渐进,直打到油圈几乎密集,剩下焦干的枯饼。俗语讲“榨上油枯个砑个”,其实是形容顺藤摸瓜,逐个追查事件起因的方式。也许“层层加码”这个词语就是由此产生的。油柱、尖码都头戴铁箍,压力由松到紧,响声由沉闷到清脆,人们“齐着力呀,哎——”的劳动号子声也愈加高亢。 如果中途有缆绳被扯断,立即由一人随时递稻草,另三人各持一股,一边扭绞,一边依逆时针方向传递,这样轮番扭绞、传递,片刻功夫就绞出一根草缆来。立屋、拆屋所需的缆绳也是这样绞成的。 第二盘油粉碾细,进甑快要蒸熟的时候,油舌上的油流不成线,而是好几秒钟才有一滴了,就要把油桶里的油“勾”出来,装入另外的器皿,以腾出油桶承接下一榨油。这里所讲的“勾”是方言里“舀”的意思。油匠师傅又要着手准备打第二榨油了。只见他一个人推着摇把往后急走几步,迅即利用物理学所讲的势能,瞄准倒贯一冲撞,倒贯滑落榨梁木背后,“砰”的一声化紧绷为松弛。随即一一拆出枯饼,用枯钻撬下油圈,另一人帮忙剥去包草,以备再次包油饼之用。俗语所讲“衙门告状口舌多,越告越紧冇奈何。若要解脱冤和恨,还靠隔壁单身婆。”所谓单身婆就是这个称为倒贯的码子。 古法榨油就是这样一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协力同心,忙而不乱,笨重而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对于新手而言,恰是一种劳动技能的培训。是一种由聚到散,又由散到聚,由松到紧,再由紧到松的过程。是一种强力拆分,再强力组合的变换。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yea.com/mfrysltx/7790.html
- 上一篇文章: 即将消逝的手工艺铁锤与炉火的守
- 下一篇文章: 田单火牛阵发生在平度市古岘镇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