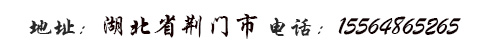江南水乡的秋天胡莹乡愁笔记
|
《一生最美的阅读笔记·乡愁笔记》 文 刘思博 返乡导师 汪成法 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上,突然生出一条岔路口,往里看去,细窄蜿蜒。岔路口的开端是一座石桥,桥头有一棵木芙蓉从侧面生长起来,花都开到了桥边的扶栏上,倒显得像是藤本植物。桥边的扶手满是风雨磨砺的痕迹,与鲜艳的花朵相配,又别有一番艺术的美。与这季节不相符合的,是桥下流水潺潺、充满生机,虽已是秋季,却拦不住戏水的野鸭游出春天的肆意。 我沿着小路向前走,耳边有呼呼的风,偶尔听见松鼠在树上跳跃发出的“嘣嘣”声,还夹杂着一些麻雀、布谷的叫声和它们扑棱翅膀的声音。路的两边,每隔一段距离就坐落着一户人家,但不管在哪,总能看见包围村庄的群山。山上多是松树和一些常绿阔叶植物,还有成片的竹子和零星分布的茶叶树,所以,尽管有一些落叶,但故乡的秋,依然是绿色的。 现在是阳历的十月初,我在外面读书,此时回来已经错过了家里收水稻的时节,虽然本来也都是机器收割,并没有什么好玩的。只见得,偶尔有人挑些夹着少许稻子的稻草在路上走,边走还边留下几颗稻谷。他们往往是家里养了鸡鸭的,把稻草带回去给鸡鸭翻腾翻腾,一来能省点收割好的稻谷,二来也算是废物利用吧。《繁昌县志》有记载:“五谷成熟皆较他县为早,每岁二月已莳种,六月中已有新谷,因春莳已种谷,故曰春谷。”繁昌县是安徽省芜湖市的一个下辖县,古时因春时种谷而得“春谷”之名,如今粮食充足,大家已不再一年种植两季水稻,都是到暮春才种、早秋便收,但因为气候的原因,这里的水稻依然比别处成熟得早些。之前听父母说,家里的水稻半个多月前就收了,如今连“晒”这个程序也都走完,收到谷仓里去了。 人都是这样,生活久了的地方,便察觉不到它的特色。一直以来,除了风景,我从未觉得我的故乡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换句话说,这里没什么习俗,也没什么特点,勉强算上过节的程序,也未必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但即使提到风景,也觉得乡村的风景都大同小异,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于是需要去别处生活,再以“游客”的身份回来看看这片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观察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重新了解那些熟悉的人。 去年这个的时候,我有机会跟着社团去南京中医药大学参观了一次,还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游览了南中医的药园。 “咦?这也是药吗?我家门口也有,我小时候摘来过家家还被扎过呢!” “这个叶子好眼熟……这不是橘子树吗?我家也种了!就是长这样的!” “啊,这不是板栗树吗?我家田里就有两棵哎!是我爸从山上挖下来的。” “这个草,我也在我们家山上见过,我还以为就是野草呢!” “啊?这就是芙蓉花啊?我们村桥头就有一棵一模一样的树,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那是芙蓉花哎!” …… 游览过程中,几乎讲解员每向我们介绍一种药材,我就要跟周围同行的伙伴表示下我的惊奇,仿佛突然得知自家喂猪的石槽其实是几百年前的古董,既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又有点喜滋滋的感觉。以至于,后来哪怕看到一些极其罕见的药材,大家也都会调侃地问我这个我家是不是也有。 现在看着路边的花花草草,从前生活的记忆、在南中医药园游览的记忆,还有眼前的光景,三种印象都重叠交织在脑海中,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从小看到大,陌生是因为它从我眼里的杂草或者野花变成了书本里见过的那些名词。这种带刺的草,和那种会粘在兔子尾巴上四处旅行的小刺球一样,都叫苍耳,也都是药材;这种野花也是有名字的,叫格桑花;这个草……叫什么我忘了,总归南中医的药园里也是有这味药材的。山上的植物品种更是数不胜数。我家就在山脚下面,所以小时候经常邀几个同伴一起爬到山上去玩,那时虽未刻意去观察,但也注意到有许多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花草。荻港是一个位于长江之畔的江南水乡小镇,而我们村庄又在荻港地势较高的地方,爬到山顶便能直接看见长江。这里土壤肥沃,空气湿润,且四季分明,适合多种植物生长,所以有这么多野生的天然药材,便也不足为奇了。这样的气候,大自然喜欢,人自然也是喜欢的。一年四季,都是故乡的农时,秋季也不例外。如今地里的棉花、玉米、黄豆、芝麻等都已经成熟了,许多人家的门口或多或少都堆着些橙黄的玉米,或者,是叶子有点蔫的黄豆杆。干活快的人家已经收完了这些作物,开始播种油菜、老蒜、青菜、萝卜之类。路上来往的人不多,三三两两不是从田里回来,就是要到田里去,少有像我这样的闲人。也有些家里不种地的,或?者家里的农活不多,还算忙得过来,便可以去山上捡些枯枝枯叶回来当柴火。 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上山的活动。冬天里,有些有经验的大人会去山上下夹子——雪地里的脚印会暴露野兔、野鸡的踪迹,冬天下夹子,只要找准了动物的脚印,往往能有所收获。三四月份,一场春雨之后,山上的茶叶树都新冒了尖,手指轻轻一扣便能克断上面的嫩芽,那时的茶叶最为香醇;夏季,蝉鸣一响,就会有人开始上山挖知了花、捡知了壳,半天下来便能收获一大水泥袋,收了三四天再拿去药店卖,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而此时,便是上山打毛栗子的好时间了。树上挂满了青色的刺球,有的已经裂开了缝,隐约可以看见里面棕褐色的板栗壳。因为毛栗子壳多肉少,再加上打毛栗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大家都只是打些回来蒸了做零食,或者烧菜烧汤放一些,不仅可以增加整道菜的鲜味,板栗本身也是香甜可口的。今年的秋,也与往年如一,并没有什么变化。人们周而复始,过着可能就会一直这样下去,岁岁年年似今朝的平淡生活。有趣的是,这种平淡并不乏味,反倒让人觉得安逸。 故乡的建筑也是极为普通的。基本都是两层的平顶房,外面统一刷的腻子粉,偶见几家红砖墙配黑色的瓦顶。听家住在东北的同学说,初来安徽时看见清一色黑白灰的建筑还觉得不习惯,他们那边的房子是各种颜色都有的,学校也多是粉色、红褐色的建筑错落着,基本是暖色调。外表看起来,这些年,故乡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只是原本在雨天会变得泥泞的土路被修成了平坦的水泥路,路边的大树似乎又长高了一点。变化最多的,大约是人。村里一共不过三十几户人家,近些年,较我大的青年人,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多已经成家立业,去县城买了房子,即使还没成家的也是在外面工作,鲜少回来;较我小的,一般也上了高中或者考上了大学,都出去读书了;有些老人身体渐渐差了,没了劳动能力,也被儿女接去城里生活了;还有一些是一整户人家都搬去别处的。农村也是不全都一样的。有的在街道边,虽然比不上城市里的车水马龙,有随处可见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但至少去菜市场买菜亦或是去超市买包盐总还是方便的,即使有些东西不容易买到,还可以网购寄到旁边的快递站。像我们村这样,被山林包围,全村连一个小卖部都没有的地方(早些年是有的,但销售量太小,最终不得不关门了),自然是留不住人的。现如今,村里只剩下一些身体还算硬朗的老人和像我父母一般在家附近打零工的中年人,没有一群小孩子打打闹闹,也没有车来车往,偶然在路上碰见的邻居也不过点头致意,又各自忙各自的去了,所以村庄里总是安静的。很多房子都门庭久闭,很多田地早已荒了没人耕作。我回家的路上恰巧遇到了几位邻居,许久未见,一下子见到了,大家总会热情地寒暄一声。才发现,谁谁谁的父亲已经一头白发,村里的胖姨现在竟消瘦了这么多,又听说谁谁谁的爷爷上个月病倒了,前几天刚过世……年轻的人走出去了,不再年轻的人还在慢慢变老。这片土地,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衰老着。 我的故乡便是一个这样普通的地方,没什么特别的习俗,也没什么值得拿出来说道的大事发生。这里的人,就这样简单地生活着,平淡无奇。只是它就像这个季节,已经走到了一年的秋天,有些叶子落下去便再也不会飘起,有些人走了便再也不会回来……城市便捷的生活拥有太大的吸引力,渐渐地,村野的故乡只能成为心中的一个印记,而不是家。 胡莹,安徽大学。我来自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的荻港镇,那是一个长江之畔的江南水乡小镇。秋景宜人,令人欢喜。只是又不免忧虑,美景如斯,孰与共赏? 我们总是去惊叹、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却往往忘记了家乡,那个我们从小生长的地方。“返乡画像”不仅是记录家乡的样貌,更多的是让人能够去发现那些悄无声息地、陪伴着自己的小美好。 《一生最美的阅读笔记》 出品 头号地标 领衔主编 李辉朱大可 人文指导 叶开出品顾问 单占生 投稿以及合作加小秘书shhxixi,或邮件至 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ufurongyea.com/mfryrybw/6701.html
- 上一篇文章: 江苏南京秦淮河名胜文化景观探讨
- 下一篇文章: 纹瓣悬铃花,锦葵科植物用途